
天津机场T2航站楼,一位中年男子对着手机屏幕反复调试角度,他的额头渗出细密汗珠——核酸报告过期了17分钟,防疫人员面无表情地重复着标准用语,身后蜿蜒的队伍开始躁动,时间在此刻凝固成冰冷的数字审判,这座承担着京津冀城市群空中门户功能的交通枢纽,每天上演着无数类似的微观戏剧,其中折射的不仅是防疫技术的精密部署,更是现代性治理下个体生命轨迹与集体安全叙事的深刻博弈。
天津机场的防疫体系堪称生物政治学的完美标本,三区两通道的隔离设计像福柯笔下的环形监狱,无处不在的监控镜头实现了凝视的弥散化,旅客的移动不再是自由的空间穿越,而成为被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报告多重数字身份所中介的资格性行为,2022年冬季奥密克戎疫情期间,机场甚至引入了抗原检测即时通关系统,旅客在落地后需在指定区域完成自测并将结果上传至云端审核——生物数据化已经细致到分子层面,这种防疫架构表面是医学需求,实则构建了一套权力运行的毛细血管网络,每个节点都行使着对身体的甄别、分类和处置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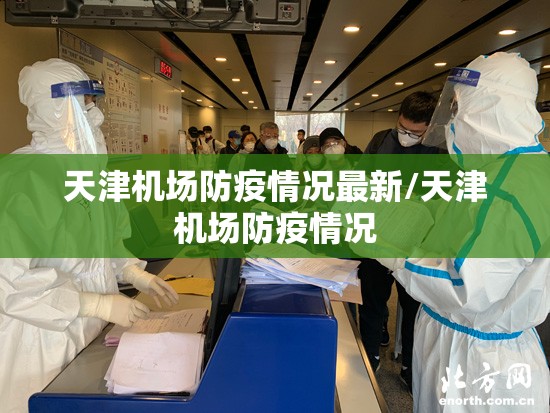
在防疫的宏大叙事中,个体叙事被迫沉默,商务人士的合同签署、留学生时隔三年的归家之旅、危重病患的跨省求医,所有这些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都在“非必要不流动”的政策话语下被扁平化为统计报表上的一个数字,一位在隔离酒店度过72小时生日的外籍工程师苦笑:“我的存在价值被简化为14天内的经纬度坐标。”这种异化过程将具身化的生命经验抽空为可管理的数据流,人的主体性在防疫优先的逻辑中被系统性悬置。
天津机场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枢纽,大量在京工作人员通过该机场实现通勤,他们的跨省流动构成特殊的管理难题,2021年初推行的“京津冀健康信息互认”机制曾带来希望,但某次局部疫情爆发后立即陷入各自为政的割裂状态,政策摇摆暴露了区域治理中的深层矛盾:一体化愿景与行政壁垒间的持久张力,当某个街道的风险等级变动可以瞬间触发数千人的行程崩溃,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在这种极端情境中暴露无遗。
耐人寻味的是,防疫技术本身正在生产新型的不平等,老年人因数字鸿沟在扫码关卡前茫然无措,外籍人士因认证系统兼容性问题滞留数小时,经济舱旅客比公务舱旅客面临更漫长的检疫等待——防疫措施无意中复制并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结构,更深刻的是,这种分级管理机制正在重塑我们对“正常”的认知:随时被追踪、经常被检测、可能被隔离,这些本属例外状态的操作,逐渐内化为生活的新常态。
随着防疫政策逐步优化,天津机场的防疫体系迎来范式转型,但后疫情时代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避免将紧急状态下的非常规手段常规化?如何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守护人的尊严与自由?这些追问不应随着隔离围挡的拆除而消失,我们需要建立更具韧性的治理模式,既能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能防止例外状态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毕竟,健康的本义不仅是身体的免于病毒,更是生命免于被过度治理的完整权利。
当最后一块行程码展板被工人卸下时,航站楼里响起零星的掌声,但比拆除物理障碍更重要的,是拆解那些深植于制度设计和集体心理中的管控思维,天津机场的防疫叙事终将翻页,但它留下的生命政治课题,仍将在现代社会的天空中持久盘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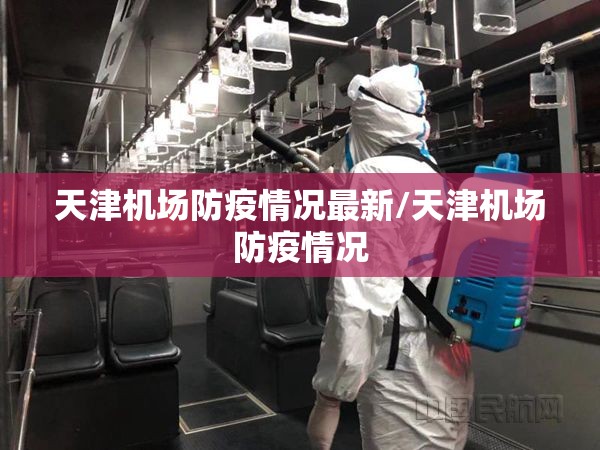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