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无形的墙正在华北平原悄然筑起,当北京卫健委宣布加强进返京管理,河南多地瞬间被划入“严控区域”,无数河南人的北上之路戛然而止,健康码依旧绿着,核酸报告依然阴性,但籍贯已成为比病毒更可怕的“原罪”,这道行政指令折射的不仅是对奥密克戎的恐惧,更是地域歧视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借尸还魂——它以科学之名,行隔离之实;以防疫为由,复活了那些本应被现代化涤荡的地域偏见幽灵。
河南与北京之间存在着近乎“中心—边缘”的依附性生态,河南常年向首都输送食品、劳务与各种基础服务,三百万河南籍务工人员编织起北京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然而政策一出,这些沉默的建设者立即沦为“高风险人群”,某建筑工地的濮阳籍工人苦笑:“我们建起了国贸三期,却突然成了首都最不欢迎的人。”数据冷酷如山:仅政策实施首周,超过12万河南籍务工者被迫延缓返京,数万家河南企业北上物流严重受阻,当防控政策未经预警地切断区域间的人口与物资流动,它所撕裂的不仅是供应链,更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基本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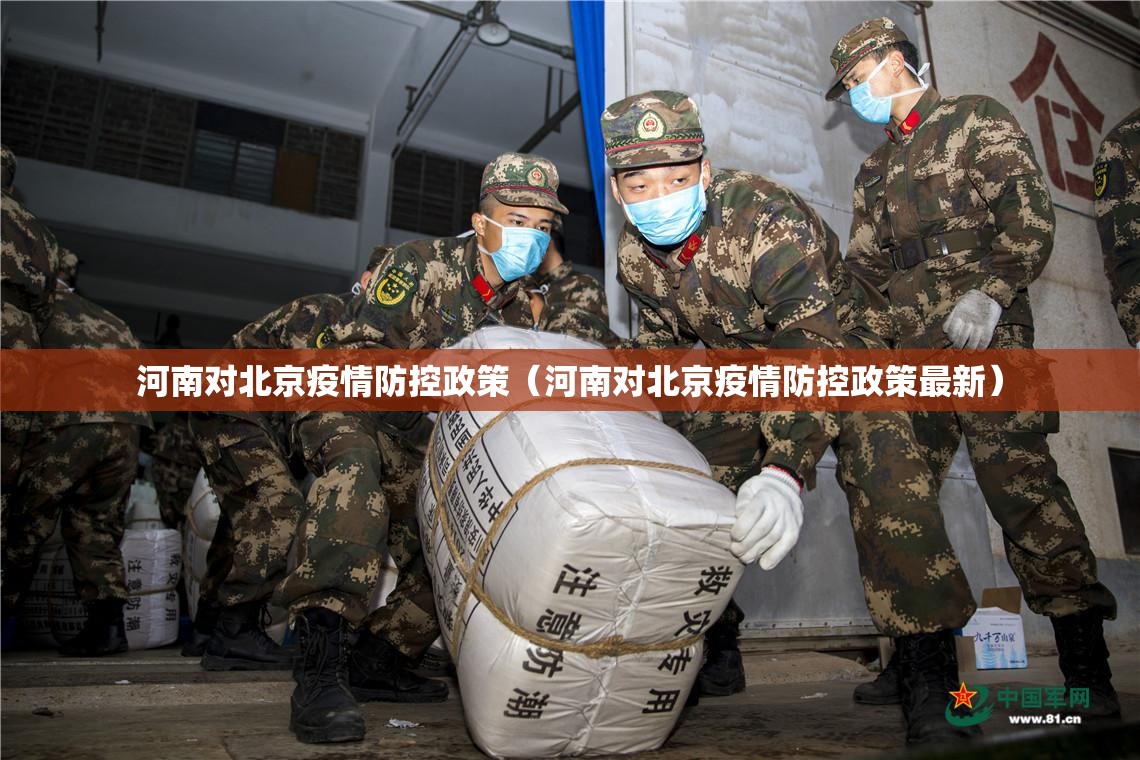
更令人忧心的是,此次决策过程中“污名化”的隐秘操作,尽管河南某市疫情散发,但省级层面阳性率仍低于万分之0.3,远逊于某些未被特殊关照的地区,然而在公共话语中,“河南”与“疫情”被刻意捆绑,形成危险能指链,社交媒体上“河南人传播病毒”的恶谑梗图泛滥,某些北京小区自发张贴“豫牌车辆禁入”——这些场景与两年前“武汉加油”的团结叙事形成残酷反讽,当地方政府将防疫责任转译为地域排斥,当危机管理退行为身份政治,我们不得不警惕汉娜·阿伦特警告的“平庸之恶”正在防疫系统中日常化、机制化。

地域歧视从来不是中国防疫叙事的新角色,2019年末武汉人在全球遭遇的排斥仍历历在目;西安封城期间对“陕北口音”的特殊排查余波未平,然而河南此次的遭遇标志着某种危险升级:歧视从民间情绪上升为制度设计,从隐性偏见转化为显性政策,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生命权力”的悖论在此显现——国家以保护生命之名,获得了对生命进行等级划分和差异化处置的权力,当河南健康的公民因籍贯被剥夺迁徙权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应急管理的失焦,更是治理伦理的滑坡。
要破除这道偏执的防疫铁幕,必须重构基于科学而非地域的精准防控范式,浙江建立的“疫情热力图”分级响应机制值得借鉴——它以街道而非省域为单位划定风险,通过大数据动态追踪而非地理出身决定流动权限,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地域平等影响评估,警惕任何可能强化刻板印象的行政措施,法治社会应当明白:最高效的防疫,永远不是最牺牲公平的防疫;最严格的管控,永远不能是最践踏尊严的管控。
河南与北京之间的这场风波揭示了中国抗疫进入深水区后的尖锐命题:当超大城市面对防控压力,是否能够以牺牲边缘群体权益为代价换取所谓安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真正的防疫共同体不应筑起基于地域的高墙,而应编织基于互助的责任网络,毕竟,病毒从不查验身份证号码前的行政区代码——人类的偏见却会,在全力以赴遏制病毒传播之时,我们更需警惕另一种社会心态的“疫情”悄然扩散,那就是以安全为名的排斥,以科学为幌的歧视,以及以集体利益为借口的制度性不公。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