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内,一批刚抵达的新疆旅客被工作人员礼貌而坚定地引导至专用通道,他们脸上的困惑与疲惫,与周围其他旅客流畅通行的画面形成刺眼对比,这不是电影场景,而是疫情防控中反复上演的现实一幕,当“来自新疆”成为比个体行程轨迹更优先的筛查标准时,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这套看似高效精准的防控体系,是否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地域歧视的深渊?在公共卫生安全与公民平等权利的天平上,权力的砝码是否已然失衡?
北京机场对新疆旅客的特殊规定,本质上构建了一套基于地理出身的风险治理术,这套技术表面上披着科学防疫的外衣,内里却遵循着前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将个体彻底溶解于地域标签的浓酸中,无论一位新疆旅客是否涉足风险区,其14天行程码如何清白,只要诞生于那片辽阔疆域,就必须接受更为严苛的检疫仪式,这种“出身论”防疫观,无异于将现代医学精准防控的基石换为古老的血统论与地理决定论,其荒谬程度堪比中世纪医生根据患者籍贯而非症状诊断黑死病,当防控政策从“管理风险区域”退行为“管理特定地域人群”,这不仅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叛,更是对现代法治理念的公然践踏。
更令人忧惧的是,这种地域标签化政策正在国家肌理上切割出难以愈合的伤痕,当新疆旅客在首都国门被迫经历一场无形的社会性隔离,其所承受的心理屈辱与认同危机远超病毒本身的威胁,他们不再是拥有丰富故事与权利的个体,而被简化为移动的“风险载体”,需要被特别监视、隔离、管控的“他者”,这种制度性区别对待,犹如一柄冷冽的手术刀,精准地割裂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形中在新疆同胞与其他地区民众之间筑起一道猜疑与隔阂的高墙,当“新疆”与“风险”在官方实践中被隐晦地划上等号,我们何以奢谈民族平等与团结?每个被单独排查的新疆人,都在承受着一种集体性的污名审判,这种创伤远比疫情更持久,更难以治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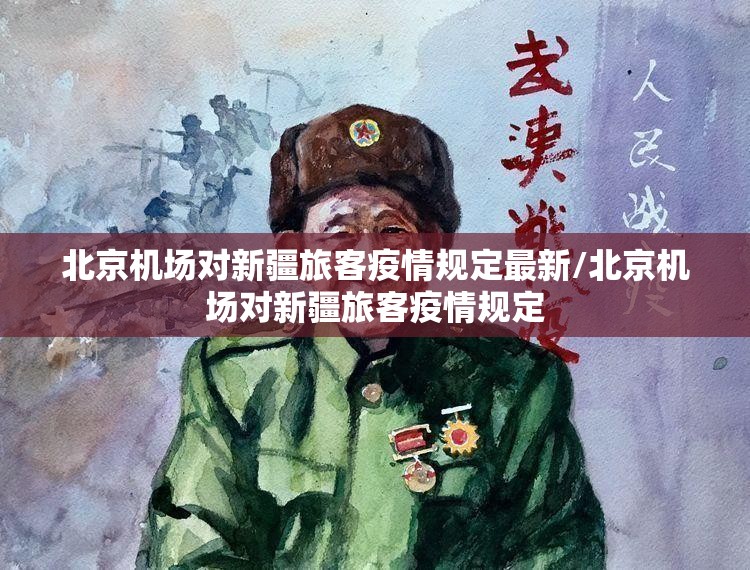
我们必须承认,北京机场的防疫困境是中国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尖锐缩影,在亿万级人口流动的巨国,面对瞬息万变的病毒,决策者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时常被迫在效率与公平、安全与自由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正是这种极端情境,才越发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成色与治理智慧,我们不能因追求短期管控便利,而牺牲社会公平的基石;不能因恐惧疫情扩散,便默许权利保障的倒退,真正的治理现代化,恰恰体现在能否在危机中坚守法治底线,能否设计出既有效防疫又最大限度尊重公民权利、避免地域污名化的精细方案。
破解此困局需要一场防疫哲学的深刻转向:从简单粗暴的地域管控,升级为真正以个体行为轨迹为核心的精准防控,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理应成为解放者而非压迫者的工具——用于精准还原每个旅客的真实风险,而非强化粗糙的地域标签,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让那些被误伤的地域群体拥有申诉与纠正的机会,防止防疫权力无限扩张而异化为地域歧视的推手。
北京机场的通道不应成为检验公民身份等级的筛子,而应是展现这个国家温度与精度的窗口,疫情终将散去,但制度留下的伤痕或遗产将长久存续,我们今日如何选择,决定了未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是否更加公正、更有尊严的社会,在防疫的天平上,每个人的权利都应有同等分量,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应该成为便利管理的代价,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穿越疫情迷雾的真正灯塔。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