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郑州街头那些蓝白相间的核酸亭如同钢铁森林里突然冒出的蘑菇,昼夜不息地吞吐着长龙般的人流,它们是秩序的象征,是数据的源泉,是庞大防疫机器最末梢的触角,然而当紧急状态解除,这些一度无所不能的微型堡垒瞬间沦为文明的废弃物,有的被废弃在街角锈迹斑斑,有的被改造为保安亭、早餐车甚至爱心驿站,上演着一场荒诞的变形记,这些沉默的金属盒子,恰似福柯笔下“异托邦”的当代化身——一个既真实存在又被社会规则割裂出来的空间,它们的功能随权力叙事的转向而被任意涂抹和重塑。
这些核酸亭的命运诡谲多变,构成了一幅国家治理术流动性的微缩景观,在紧急状态下,它们是国家毛细血管末梢的权力节点,是生成“可读性”的数据工厂,将流动不安的生命固化为清晰可控的统计数字,每一个拭子采集都是一次微型的规训仪式,将个体纳入宏大的健康监控网络,然而当治理逻辑从“例外”切换回“常态”,这些高度特化的装置立刻暴露出其功能的单一与脆弱,它们的转型——或被回收、或被遗弃、或被赋予全新使命——赤裸裸地揭示了治理技术的内在暴力:其存在价值完全由瞬时目的决定,一旦任务完成,依附于其上的结构与意义即刻蒸发,留下空洞的物理残骸等待下一次征用,这种装置随政策指令而生的急速功能转换,暴露了技术治理工具理性下隐藏的挥霍性与临时性。
核酸亭幽灵般的残留存在持续向城市散发着治理的隐性记忆,它们从“保护者”象征到“废弃铁皮”的坠落轨迹,构成了一部无言的微观权力变迁史,市民经过这些改造后的亭子时,会经历一种奇异的认知失调:眼前的早餐车无法完全掩盖它曾经作为核酸采样点的记忆痕迹,两种截然相反的治理意象——生命健康的监控与日常生活的滋养——在同一物体上重叠碰撞,这种时空压缩体验形成了德勒兹所言的“控制社会”生动隐喻:治理不再依赖高墙耸立的封闭设施,而是通过灵活、分散、可流动且功能可随时刷新的模块化装置渗透入生活褶皱,它们潜伏于日常场景中,静候下一次危机的召唤以激活全新功能。

透过郑州街头这些被废弃或改造的核酸亭,我们得以窥见现代性治理中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追求精准与高效的技术工具主义,反而生产出巨大的临时性浪费与功能冗余,这些微小建筑的生与死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政治哲学困境:当国家运用庞大资源迅速构建应急基础设施时,是否应考虑其超越即时危机的生命价值与可持续性?治理的智慧或许不仅体现在紧急状态的雷霆响应,更在于如何将临时性装置转化为滋养日常生活的永久性资产,从而在秩序与自由、效率与人文之间找到平衡点。
核酸亭的幽灵仍在郑州街头低语,它们既是刚刚过去的集体创伤的纪念碑,也是未来潜在风险的预演场,读懂这些金属盒子的前世今生,便是解读一部国家与个体在非常态与常态间不断协商、博弈与适应的微观政治学,治理现代化的真正考验,或许不在于能多快地建造无数核酸亭,而在于如何智慧地让这些亭子——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治理模式——在使命结束后,依然能有机融入市民生活的肌理,成为延续的城市记忆而非刺眼的时代疤痕,当技术治理的浪潮退去,留下的不应仅是锈迹斑斑的空壳,而应是能够滋养社会韧性的人文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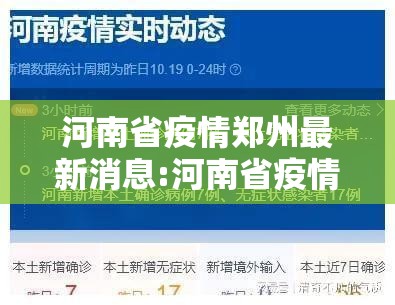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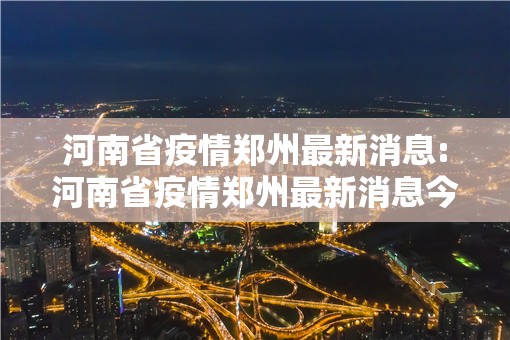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