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深秋,郑州街头空无一人,二七塔的钟声依旧整点响起,却失去了往昔下方熙攘人群的呼应,这座素有“铁路拉来的城市”之称的交通枢纽,在疫情反复的三年间,经历了数次静默管理,每一次封闭时间表的启动,都是对城市治理能力与市民生活韧性的双重考验。
郑州首次大规模封闭管理可追溯至2020年春节,与武汉封城几乎同步,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当时为期28天的严格管控,创造了郑州版本的“小汤山”模式——仅用10天建成岐伯山医院,这种“郑州速度”既展现了应急响应能力,也折射出疫情初期人们对病毒认知的有限与应对的仓促。
2021年夏季的暴雨灾害与疫情叠加,让郑州面临双重考验,7月30日宣布的封闭管理与灾后重建交织,形成特殊的历史叠影,金水区某社区主任回忆:“我们刚从地下室抽完水,就立即组织核酸检测,居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排队,没有人抱怨。”这种多重压力下的集体耐力,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2022年秋季的封闭管理则更具代表性,10月中旬起,郑州先后对中原区、二七区等区域实施静态管理,最长持续达42天,与早期封控不同,这次管理更加精准化——以小区为单位划分高、低风险区,建立“白名单”保供体系,京东物流的王师傅戴着N95口罩告诉记者:“我那一个月睡了30天驾驶室,但保证了封控区每家都有菜。”
封闭时间不仅改变了空间秩序,更重构了时间体验,对于居家办公者,时间变得弹性而模糊;对于一线防疫人员,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值班时段;对于学龄儿童,时间被网课和核酸采样重新定义,郑东新区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显示,封控期间咨询量增加47%,主要问题为时间感知紊乱带来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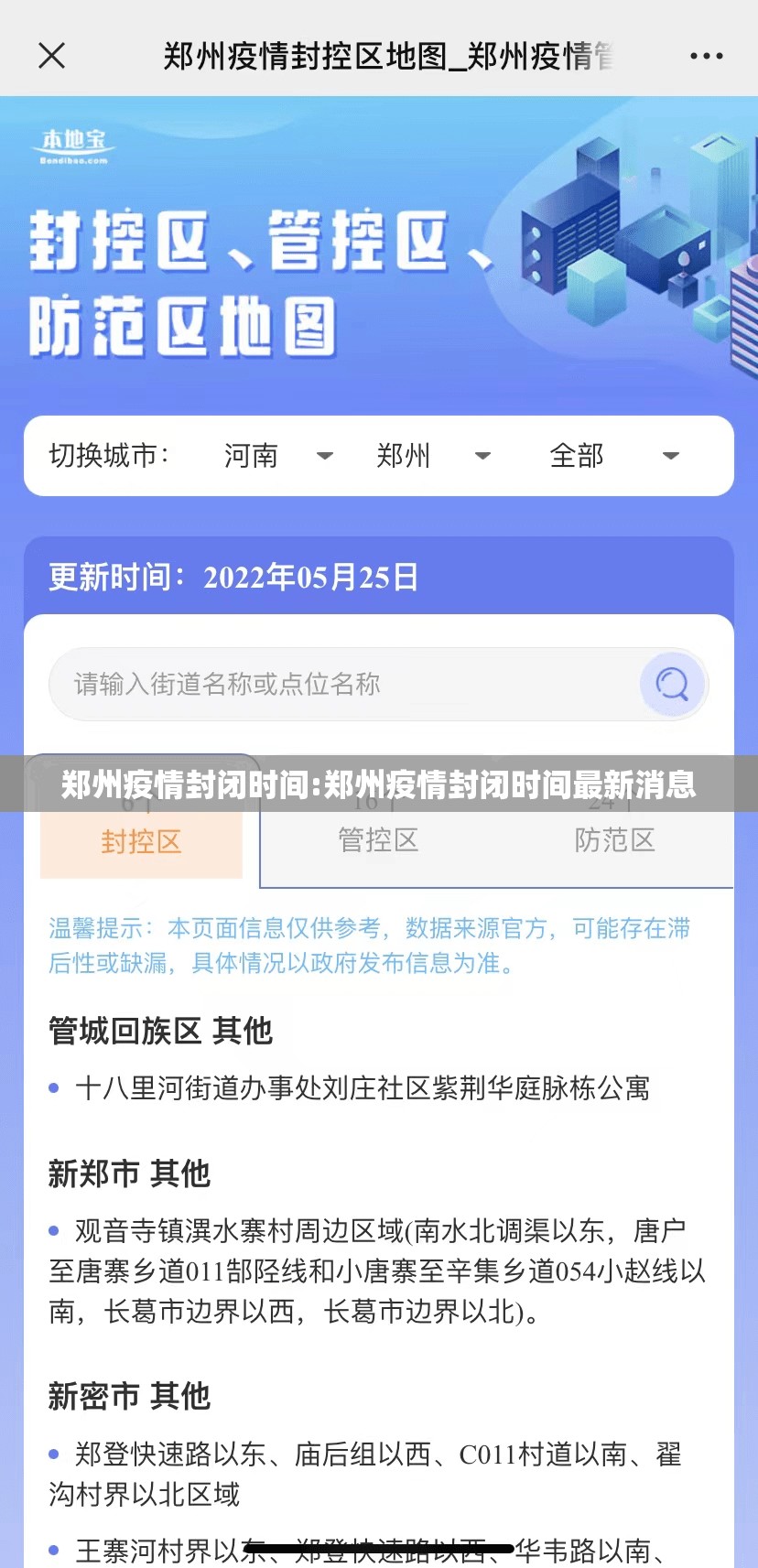
微观生活中的时间叙事同样值得记录,大学路某面包店老板开发了“三日保鲜装”产品,巧妙对应核酸检测有效期;新婚夫妇通过微信群举行“云端婚礼”,将仪式时间压缩为20分钟;社区志愿者发明了“换岗时间银行”,用服务时长兑换未来休息时间,这些民间智慧创造了特殊时期的时间管理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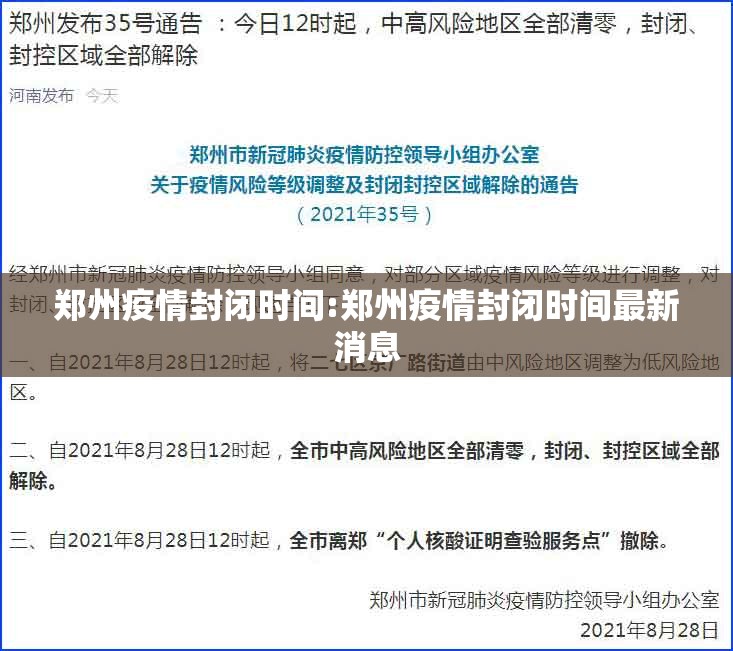
经济维度的时间损失则更为直观,郑州GDP在2022年第四季度同比仅增长0.8%,餐饮业营业额下降52.3%,但与此同时,本地电商平台交易额增长213%,预制菜配送时间从 pre-pandemic 的2小时缩短至28分钟,封闭时间在摧毁某些行业的同时,也加速了新经济形态的成熟。
与武汉、西安等城市的封控相比,郑州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交通枢纽地位,作为全国铁路网中心,郑州的封闭管理会产生连锁反应,2022年11月的封控期间,郑州站每日仅保留8对列车,大量货车滞留编组站,铁路职工创造了“接力驾驶”模式,实现“人员不接触、货物不断流”,这种创新源于对时间效率的极致追求。
当2023年春天全面解封来临,郑州人迎来了“被偷走的时间”的回归,但很多改变已成为永久印记:老年人保持的扫码习惯、企业保留的远程办公选项、学校完善的双线教学方案,这些疫情时期的“时间遗产”,仍在持续塑造着城市的生活节奏。
郑州的疫情封闭时间史,是一部城市应对危机的进化史,从最初的全城静默到后期的精准管控,从单纯防控到统筹经济发展,每一次封闭都是对治理体系的压力测试,这些特殊的时间片段如同地质分层,记录着城市在非常状态下的适应与创新,最终凝聚成郑州人独特的集体记忆——关于困境中的相互守望,关于限制条件下的生命韧性,关于暂停与重启之间的永恒辩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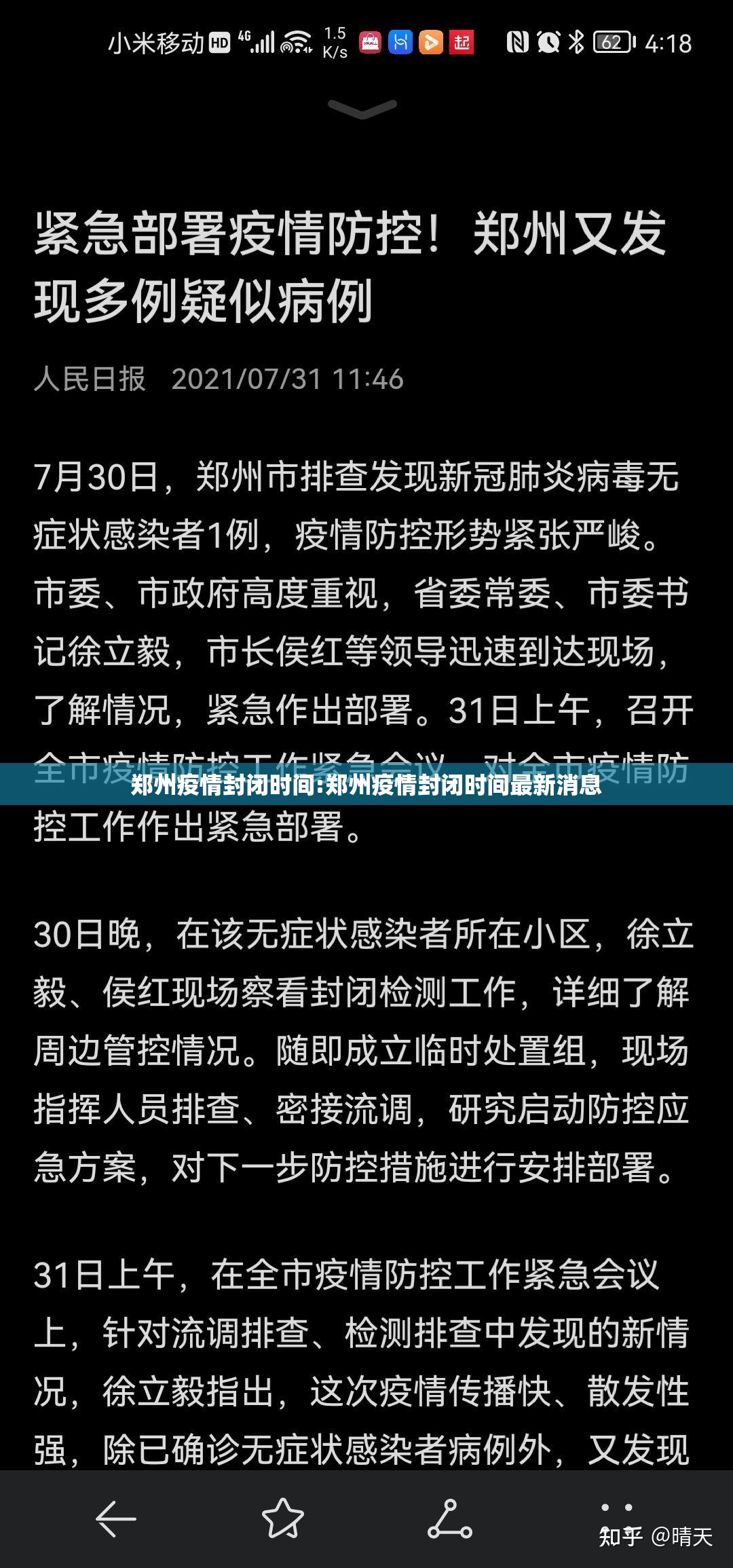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