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街头,霓虹依旧闪烁,却少了往日的喧嚣,赌场门口,保安严格查验着游客的“健康码”,那些曾经挥金如土的面孔被简化为绿、黄、红三种颜色,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瑞丽边境线上,边防人员正24小时轮班值守,严防奥密克戎变异株跨越国境线,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却在同一时刻面临着相似的抉择:如何在疫情防控与民生保障之间寻找那个几乎不可能完美的平衡点。
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宣布,将根据疫情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防控措施,建立“精准防控”机制,这套系统将澳门划分为不同风险区域,对应不同强度的管控要求,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套科学、理性的管理体系;它正悄然重塑着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态,赌场员工李某苦笑着说:“现在不是人选择赌桌,是健康码决定你能走到哪张赌桌。”餐饮店主李女士则面临更现实的困境:“防疫要求不断变化,今天我还能堂食,明天可能就只能外带,采购计划和员工排班全都乱了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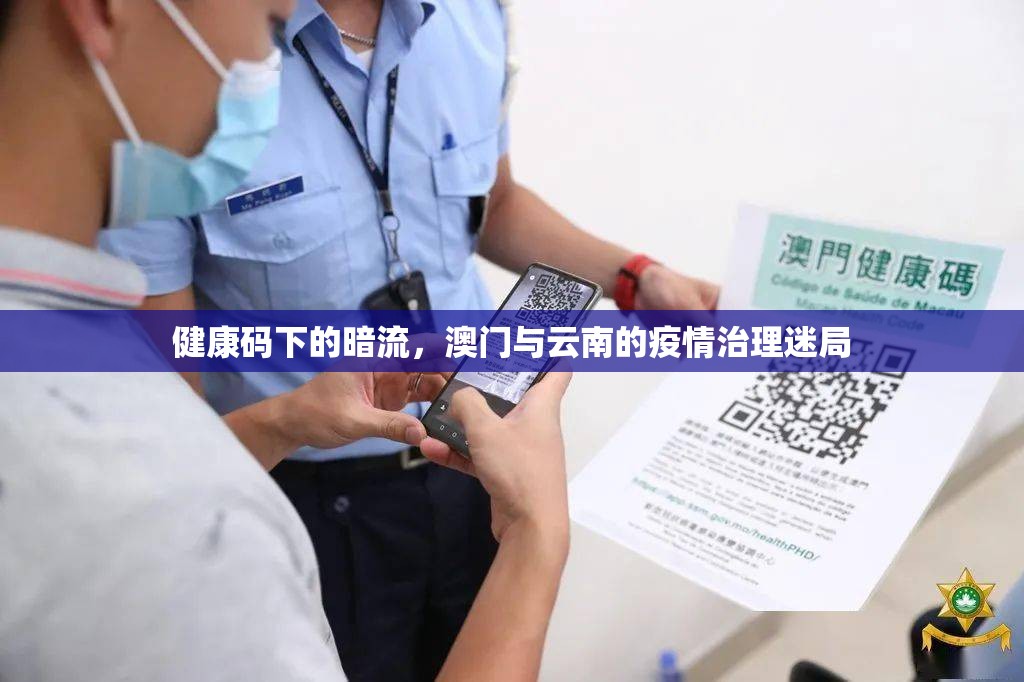
云南省发布了最新疫情防控通告,强调“非必要不外出”原则,同时对边境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在中缅边境的姐告口岸,曾经繁忙的跨境贸易如今只剩下零星车辆通行,边民互市几乎停摆,靠跨境贸易为生的商户们面临生存危机,来自瑞丽的香蕉种植户李先生说:“我们的香蕉运不出去,外面的生产资料进不来,这一年算是白干了。”
两地的防疫政策在技术层面上堪称精密,澳门依托其高度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实现了防控措施的快速部署与调整;云南则依靠网格化管理与群众动员,构建起一道道“防疫长城”,这种技术治理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暴力——当个体的生活被简化为数据流中的二进制代码,当复杂的社会需求被压缩为防疫指标,我们正在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澳门,那些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突然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在云南偏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因为语言障碍难以理解迅速变化的防疫要求,这些群体正在成为疫情防控中的“新隐形人”,他们的需求与困境被淹没在宏观的防疫叙事中,社会学家警告,这种“一刀切”的政策执行正在加剧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更令人担忧的是,持续不断的疫情防控正在重塑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抗疫包”发放和经济援助计划,强化了对市民生活的直接干预;在云南,严密的边境管控扩展了国家的治理边界,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生命权力”理论正在这里以现代形式上演——国家权力通过管理生命过程(健康、安全)来实施控制,而这种控制因为其“保护性”而获得了广泛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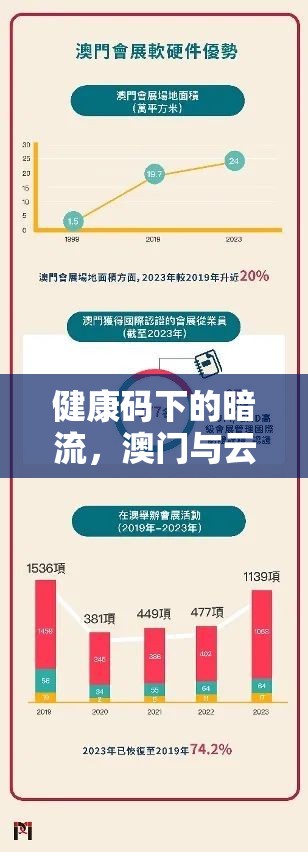
疫情防控还创造了新的语言体系,澳门市民见面不再问“吃了吗”,而是互相询问“你绿了吗”;云南边境村民谈论的不再是收成,而是“核酸有效期”,这些新词汇不仅反映了生活重心的转移,更标志着一种新社会规训的形成——我们正在不自觉中将防疫逻辑内化为日常思维。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否需要反思:当防疫从应急措施转变为常态治理,当健康码从临时工具变为永久存在,我们是否正在无意中构建一个以“安全”为名的监控社会?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在这里呈现出双重性:我们既面临病毒带来的风险,又面临过度防控带来的社会风险。
澳门与云南的案例提醒我们,疫情防控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治理命题,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如何消灭病毒,而在于如何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不杀死那些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自主性、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场持久的疫情战争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疫苗和核酸,更需要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持续反思与革新。
在健康码的绿光背后,在边境防控网的阴影之下,保持对社会异化现象的警惕与批判,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毕竟,疫情终将过去,而它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长期与我们共存。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