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深秋,乌鲁木齐新冠疫情牵动人心,当市民们刷着手机查看每日疫情通报时,一则简短的消息引发思考:“11月12日0-24时,乌鲁木齐市新增确诊病例20例,无症状感染者380例”,许多人不禁追问:这些确诊人员具体信息为何不详细公布?是哪些小区?什么职业?活动轨迹如何?这背后实际上涉及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隐私权的复杂平衡。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依法履行疫情信息公布职责,乌鲁木齐疫情信息发布遵循了这一原则,每日公布确诊病例数量、分布区域等基本数据,确保公众知情权得到基本保障,公布确诊人员“具体信息”却存在明确法律限制。《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将医疗健康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这意味着,随意公开确诊者详细个人信息可能构成违法。
从公共卫生角度考量,适度公布病例相关信息的益处显而易见,2020年初期,各地公布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有效帮助了潜在接触者及时采取隔离措施,遏制了疫情扩散,乌鲁木齐部分区域在疫情期间也会公布风险区域和流调信息,使居民能够评估自身风险,采取相应防护,这种基于公共卫生需要的有限度信息披露,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工具。
信息过度公开的代价不容忽视,疫情初期,某些地区曾发生过确诊患者个人信息遭全网曝光的事件,导致当事人遭受网络暴力和社会歧视,有的患者被贴上“毒王”标签,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在微信群广泛传播,这种过度曝光不仅侵犯个人尊严,还可能引发民众恐惧就诊的心理,反而不利于疫情监测与控制。

乌鲁木齐在疫情信息处理上采取了相对平衡的做法——既公布足够信息让公众了解疫情态势和风险区域,又保护确诊者个人隐私不被过度暴露,这种“有限透明”模式遵循了比例原则:只收集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必要信息,只向有需要机构提供必要数据,只公开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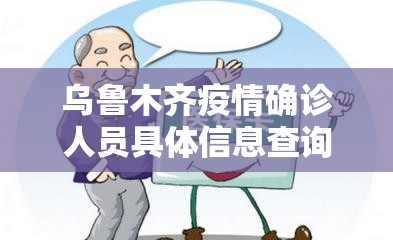
全球范围内,疫情信息处理存在不同模式,韩国采用高度透明方式,公布详细到餐厅名称的行程轨迹;新加坡则只公布必要流行病学信息而不透露可识别个人身份的资料,不同选择反映了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和社会价值观上的差异,中国采取的是中间路线,既不是完全透明也不是完全不透明,而是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公民隐私。
对于乌鲁木齐市民而言,理性看待疫情信息至关重要,我们既需要关注疫情动态,配合流调工作,也应尊重确诊者隐私,避免对患者进行道德指责,社会应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确保信息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之间的必要共享,同时防止个人信息被滥用。
乌鲁木齐疫情终将过去,但如何平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透明与隐私保护,将是长期命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们既要依靠科学防控,也需要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指引,只有当每一位市民的权益都得到充分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构建起牢固的公共卫生防线。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